
“要是世界上没有花粉那该多好!”不少深受花粉症困扰的人如此心心念念着。
人类已经与花粉症“相爱相杀”几万年,从19世纪开始,医生一边为神秘的新病症伤神,一边艰辛努力查明真相。花粉症也许不是单纯的植物学原因导致,而有着更复杂的理由。
研究发现,人类过分干预自然,导致生态系统失衡,某种特定的植物会在机缘巧合之下跨越国界、野蛮生长,人类与自然本来良好的关系出现了裂缝,从花粉症的“小历史”中也可以读出“大历史”。
本文摘自《花粉症与人类:让人“痛哭流涕”的小历史》,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为被错怪的花粉“翻案”
凛冬将尽,花鸟鱼虫一同讴歌春天的到来。在这个美好季节到来之际,为什么只有我们那么难受呢?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受到花粉的洗礼。
日本及欧美地区这些温带国家要忍受暴雪般的漫天花粉——新年到春天有榛果、杉树、扁柏、柳树、杨树、山毛榉、白桦等树木花粉,初夏到盛夏有稻科的牧草、谷物花粉,晚夏到晚秋有豚草、魁蒿等菊科杂草花粉。而地中海地区的法国南部、意大利有柏树花粉,以色列、土耳其有橄榄树花粉,中东的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有枣椰树、牧豆树花粉,印度及东南亚地区有甘蔗、椰树花粉,中国(尤其是南京)、伊朗有悬铃木花粉……世界各地都有当地常见的花粉症。更令人吃惊的是,就连南极竟然也有花粉飘扬。
这么看来,我们无论躲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有可能被花粉弄得“痛哭流涕”、鼻塞难忍。当然,花粉症是死不了人的,但取而代之的是要一直被花粉折磨。啊!花粉!你这个“人生伴侣”实在太可怕了!但是,花粉其实也很冤枉,毕竟远古之时,远在人类踏足陆地之前,它们(“花粉”这个词在印欧语系中多为阳性名词)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说它们是陆地的原住民之一。况且人类与花粉的邂逅本来就是温情脉脉的。截至近代,文人墨客都会从花粉中获取灵感,生物学家则着迷于花粉的形成及释放等机制,真可谓“你侬我侬”。
所以说,花粉还是那个花粉,只是我们现代人变了而已。最初我是怀着一肚子火,为了消灭掉那可恨的杉树花粉才开始从事花粉研究的,想不到却被花粉的魅力所折服,想给一直被人们错怪、唯恐避之不及的花粉“翻案”。
植物的世界秩序井然
那为什么瓜藤不会结出茄子呢?德国植物学家科尔罗伊德(1733—1806)看到炼金术师用铁和铜炼金,于是在想:生物学范畴里是不是也能通过某种手段让金丝雀变成孔雀呢?为了验证这个猜想,他先从植物交配实验着手。1760年他成功培育出了人工杂交烟草,但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异常现象在自然界是不会发生的:“造物主给自然界定制了一套精巧绝伦的法则,用以预防失序和混乱的产生。这套法则就是同种花粉和异种花粉即使同时沾在柱头上,也只有同种花粉会受精,异种花粉会受到排斥。”
换言之,瓜藤上不会结出茄子,是因为瓜的雌花即使沾上了茄子的花粉也不会受精。科尔罗伊德在花粉中看到了上帝造物的秩序,内心的震撼洋溢在话语之中。
在花粉出现之前,像蕨类这样通过孢子繁殖的植物在地球上独领风骚。我们必须对这些蕨类植物心怀感激,因为它们创造出了人类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原动力——煤炭。孢子繁殖需要水,所以孢子植物天生就不能离开水边太远。后来,裸子植物出现了,它们能够借助风力传播花粉,使其子子孙孙能够轻而易举地到达干燥的内陆地区。
花粉是信息的宝库
古生物学知识告诉我们,花粉诞生于侏罗纪,那时候还没有人类,恐龙在地球上昂首阔步。然而,后来花粉传播成为绝大多数植物选择的繁衍方式。没办法像动物那样到处行走的植物,发展出了独特的能力,它们将继承自祖先的各种遗传信息封印在肉眼不可见的黄色小微粒里随风而去,有时候甚至能飘到数百公里开外。这一粒粒朴实无华、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生命气息的粉末里,竟然凝缩着植物自身蕴藏的精华。
正如不同种类植物的花朵有不同的美,不同种类植物的花粉也有着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模样,因此我们只需要看一眼花粉,就能够倒推这是哪种植物。花粉就像是植物的身份证,每一种花粉都有独一无二的个性印记。花粉的这种个性已经在地下沉睡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有些甚至长达数千万年。
花粉和孢子的外壁由一种化学性质极其稳定的高分子碳素物质构成。这种物质叫孢粉素,用盐酸、氢氧化钠等强酸、强碱都没法溶解。所以很多时候科学家用酸、碱、氢氟酸等物质处理完沼泽、湿地的泥土之后,还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保存完好的古代花粉或孢子。换言之,如果我们调查残存在地层中的花粉,或许就能够推测出过去的各种信息。
这种花粉分析的学问被称为孢粉学,通过孢粉学的分析,我们能够绘制出土壤中的花粉分布图,从量化角度分析过去的植被变迁,还能推测当时的气候变动。换言之,花粉能为我们提供有关人类农业起源及随之而来的植被破坏情况、石油和煤炭开采情况及环境变化情况等信息。例如冢田松雄在《花粉会说话》中就提到,通过分析永冻土层下埋藏的猛犸象牙齿上和胃部里残留的花粉,我们就能知道这只猛犸象是在哪个季节变成冰雕的。在现代,警方甚至能够通过沾在衣服、鞋底上的花粉来定位杀人犯。同理,通过孢粉学分析,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能推算出人类是在何时与花粉邂逅的。
曾是高贵的身份象征
曾经,花粉症变成了贵族阶级的身份象征。
1887年,出生于苏格兰的伦敦医院临床医学名誉教授安德烈·克拉克爵士(1826—1893)在西伦敦内外科学会上公开说:“花粉症选择了知识分子而非文盲,选择了绅士而非粗人,选择了达官显贵而非坊间小丑……”
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知识阶层经年累月地接受系统性职业训练,埋首于书山文海中,导致神经强度减退,易感花粉。夏季卡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神经疾病。此外,农业革命之后,耕地和牧草的栽种面积扩大也是致病花粉增加的其中一个原因。而农民群体由于平日里就一直和花粉打交道,已经适应了,也就对此免疫。
美国神经病学专家乔治·米勒·比尔德(1839—1883)认为易患花粉症的典型体质特征包括“纤细柔顺的头发、娇嫩的肌肤、深邃的脸孔、小骨架、肌肉力量弱、聪明、积极进取但又情绪化的性格”。
中世纪时期,人们认为玫瑰伤寒是疑难杂症,只有体质特殊的人才会对玫瑰花过敏。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花粉症研究之父”查尔斯·布莱克利认为当时流行的牧草花粉症是在城市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上流社会的精英罹患的一种精神疾病。而比尔德向社会普及了“神经衰弱”这个词,他在《美国的神经疾病》中提出,对气候变化、食物、药物等刺激性物质过度反应的神经过敏体质是因为现代文明而产生的。
是医学课题,也是社会问题
布莱克利说过,花粉症不是一种可致死的急性病,我们完全可以留出足够安全的时间慢慢对付它。
回首人类史,才发现曾经以文明病出现在现代人面前的花粉症,现在已经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害病了。人类过分干预自然,导致了生态系统失衡,某种特定的植物在机缘巧合之下跨越了国界,野蛮生长,让人类与自然本来良好的关系出现了裂缝。我们应该能说,花粉症既是医学课题,也是环境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经济、科技问题。
1906年,奥地利儿科医生克莱蒙斯·冯·皮尔凯(1874—1929)发明了“过敏”这个词,他说:“我们经常会忘记疾病才是锻炼免疫的唯一手段。正因为会生病,生物才获得了‘免疫’这个好处。”我们不要想着根除疾病,而是要想着如何与疾病共存,以疾病为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能根除花粉症的话,那么在我们完全扑灭花粉症等过敏性疾病的那一瞬间,我们就将自己暴露在另一个新生的免疫性疾病之下了。
早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时,英国耳鼻喉科医生莫雷尔·麦肯基曾预言:“当自然被机械取代之际,能让人类知道世上存在过花朵的,就只剩下植物博物馆里那些干巴巴的标本了。没有了花粉,花粉症也就随之消失了。”
但是我确信最终活下来的是花粉而不是人类。1940年,花粉学领域的巨擘罗杰·菲利普·伍德豪斯就说过:“在五月花号到达的几千年前,豚草就已经扎根在新世界的土地上了。我相信,只要人类不再破坏这个星球,豚草就还能在这里再扎根个几千年。”
当你的花粉症变得严重时,愿你能抬头,眺望天空中的花粉光环。花粉光环是大自然送给它那任性的组成部分——现代人的一条信息。
我们想给下一代留下一个美好世界,要如何迈出这一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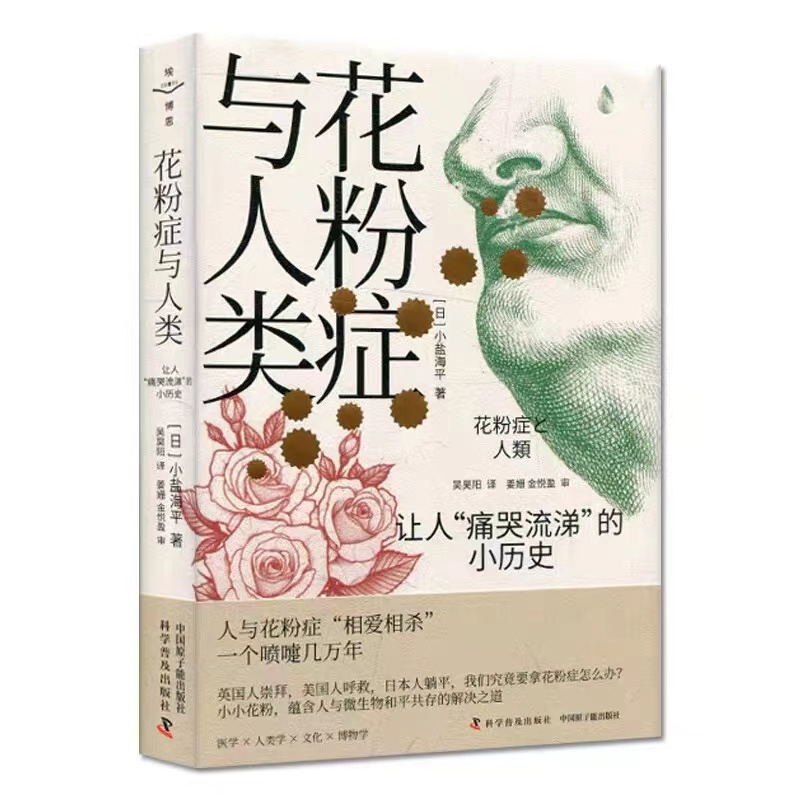
《花粉症与人类:让人“痛哭流涕”的小历史》
[日]小盐海平 著
吴昊阳 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